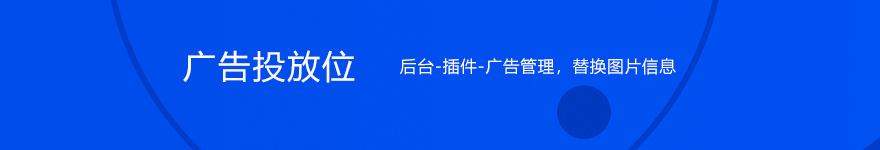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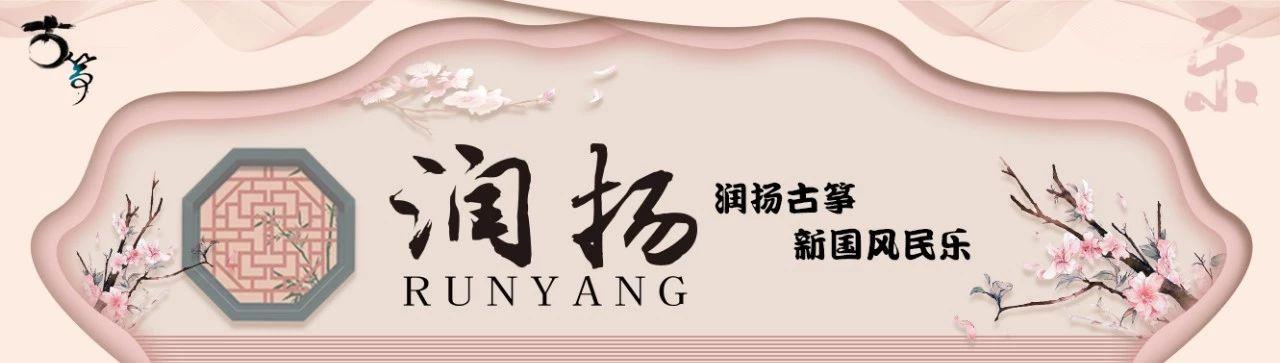
每一個領域都是一個“江湖”,古箏圈也不例外,江湖中各路高手云集,你方唱罷我登場,上演傳奇,有人憑借出眾才華,在21根弦上恣意揮灑,為往圣繼絕學;有人倚仗求索精神,在風雨飄搖的年月里砥柱中流。
今天給各位箏友們講講四位古箏泰斗鮮為人知的一點軼事,繼往開來,雖然時代不同、潮流不同,但總有些東西可以跨越時代,情懷不衰。
趙登山:古箏是他改寫命運的魔術棒
趙登山先生1933年出生于菏澤市,中國音樂家協會會員,中國古箏學會副會長,國家一級演奏家,中國著名民族樂器演奏家、作曲家、教育家。
“文革”期間,趙登山被下放到農村 ,做了一名炊事員 。利用閑暇時間 ,他學京胡 ,唱京戲,為周圍同事表演 。由于他多才多藝 ,成了最受人們喜歡的炊事員。
有一年,趙登山所在的吉林歌劇舞劇院接到上級任務 ,要為來訪的西哈努克親王演出 。領導找不到合適的人選,忽然想到了下放當炊事員的趙登山 。他們派人找到趙登山,想讓他趕緊創作曲目并表演箏曲 ,甚至連作曲的任務也落在了他的頭上。可是那時趙登山的古箏早已棄置多年,加之沒有適合的曲目可彈奏 ,但趙登山也只好臨危受命 ,重操舊業。
當時團里連一架完整的古箏都找不到 ,他只好到團里的倉庫里尋覓樂器。在犄角旮旯中 ,他找到一架殘破不堪的古箏,然后修補拾掇 。沒有琴弦 ,他只好將斷弦連接在一起 。在很短的時間內 ,趙登山排練了經過重新編配的東北民歌 《公社春來早》 ,并找來一位拉二胡的同事給他伴奏。由于西哈努克精通音樂 ,自己還會作曲,于是趙登山就和同事商量在演出中演奏一首西哈努克寫的歌頌中柬友誼的作品。

為了使演出效果突出 ,趙登山在古箏上欲模仿獨弦琴顫音的音色 。經過不斷摸索,他發明了揉弦泛音的手法 ,終于模仿出了獨弦琴的顫音效果。當晚演出中,西哈努克聽到自己的作品在中國音樂家的精心演繹下別具韻味,十分激動。剛演奏到第三樂句時 ,西哈努克便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起身熱烈鼓掌,全場觀眾也隨之起立鼓掌,場面十分熱烈。
通過這次成功的演出,趙登山結束了當炊事員的生涯,又開始了與箏為伍的漫長歲月。可以說,這一曲古箏改變了趙登山顛沛流離的命運。
趙曼琴:潛心習箏,始于同行嘲笑
趙曼琴,1953年出生于南陽。中國音樂家協會會員、古箏藝術專修院院長、黃河科技大學音樂學院教授、中奧維也納音樂學院客座教授。
趙教授曾分別在省級和國家級音樂評獎中獲演奏一等獎和作曲一等獎,多首作品被全國各考級組織列為古箏考級高級曲目,或作為國際比賽決賽指定曲目,并曾應邀出訪日本演出,在香港舉辦個人作品音樂會。
他曾講述過觸動自己去研究、創立快速指序技法的經歷。

在趙曼琴剛剛到河南省新野文工團工作的時候,他自己已經能夠彈不少古箏獨奏曲,并且已經能寫作一些歌曲和簡單的古箏獨奏曲了,因此自我感覺相當良好。誰知道第一次參加樂隊排練,他的優越感和自尊心就被打了個粉碎。
當時是個中西結合的混合樂隊,由于作曲者不懂古箏的性能,在配器時讓古箏和揚琴、小提琴、二胡演奏同樣的旋律。演奏開始時,趙曼琴甚至還沒來得及看清楚前兩小節的譜子、沒想出這種音型用什么指法彈奏,樂隊風馳電閃般的旋律已經在他耳旁一掠而過,他自己甚至找不到樂隊已經演奏到哪一小節,茫然無措的手指不知該放到哪根弦上才好,那種窘迫、難堪、孤獨、絕望感令他至今難忘。
不出意外,趙曼琴受到了樂隊同行不少的挖苦和嘲笑,用他們的話說就是“不夠吃”,意思是學的本事不夠用。

后來趙曼琴請教了一些彈古箏的同行,他們都說這就不是古箏應該彈的旋律。說到別人嘲笑時,大家都說,“別理他們,他們不懂古箏”。但趙曼琴無法忘掉每當自己坐在樂隊中看著其他樂器的演奏員忙忙碌碌而自己卻無所事事時,都感覺自己像濫竽充數的南郭先生一樣厚顏無恥,并且為古箏演奏技法的貧乏而感到羞愧。
于是,他下定決心,暗自發誓,一定要研究一種新演奏技法,改變古箏在樂隊中的色彩樂器地位,使古箏能與別的樂器一樣成為常奏樂器。他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帶著這樣的心態開始研究解決古箏的快速演奏問題直到現在的。
王中山:練琴是自己防止挨揍的絕招
王中山,著名古箏演奏家,中國音樂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 ,國樂系副主任。中國音樂家協會理事,中國音樂家協會古箏學會會長,中國音協社會音樂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民族管弦樂學會古箏專業委員會執行會長。
在接受采訪時,古箏大師王中山曾自述小時練琴挨打趣聞。

王中山兄弟三人,他是挨打最少的,并不是因為王中山很乖,而是因為他很巧妙。每當他們淘氣,父母準備教訓他們的時候,王中山最先發現,于是他就老老實實地趕快去練琴。而且通過從小練琴培養出來很好的聽覺,老遠就能從眾多人的腳步聲中聽出來父親的腳步聲。當感知到父親過來了,他就趕緊竄到房間開始練,用這種方式就很少會挨打了。
王中山是音樂世家,除了他爸媽不懂音樂。所以他還經常會用我的辦法來糊弄家長,比如今天老師教他《高山流水》但他不會彈,我就彈個《漁舟唱晚》給父親聽,父親覺得彈得很熟練,所以就躲過去挨揍了,這就是小時候的王中山和父親斗智斗勇的故事。

曹正:古箏大師也愛塤
曹正,一代古箏教育家、理論家、演奏家、中國古箏院校事業的奠基人,中國古箏一代宗師,中國音樂學院教授。
從20世紀40年代中期以來,曹正借鑒古琴指法,設計了箏演奏指法符號,并將工尺譜譯成簡譜和五線譜教學(目前海內外所出版的箏書中,大多以此作為依據),對箏曲的傳播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但今天的故事,卻是曹大師與塤的故事。
道德學社期間,曹正在北平見到過塤,很喜歡(當時的北平塤是很少見的)。他見到的塤很可能是7孔的,覺得十分新奇,并決定親自動手制作陶塤(仿古)。這在當時是一個新的領域,生活周圍無人涉足此道,實踐中更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依循。
20世紀40年代初曹正回到河北昌黎教小學,學校附近有個瓦盆窯,他試制塤的念頭就更加強烈了。便常常帶著學生到海邊,大家一起動手在沙灘上挖個大坑,到四五尺深時,膠泥出現了。他教孩子們用膠泥做塤、筆筒和其他小東西,然后拿到窯上燒制,孩子們對此很感興趣。
這種教學模式為我們今天的多樣教學提供了參考。假期他到北平繼續查找資料,經過不斷嘗試,終于在1943至1944年期間試制成功了七孔仿古陶塤。
1964年秋,中國音樂學院在北京成立,曹正應邀至該院從事古箏教學與研究工作。1979年評為副教授,1981年評為教授,古箏教學及社會活動日益繁忙,但他從未間斷過對塤的研制和改革。

1981至1982年,邱大成(第一個古箏專業研究生)與王明君(中國音樂學院竹笛專業學生)在電臺演奏了曹正改編的塤與古箏二重奏《高山流水》和《水龍吟》。
1982年曹正開始進行增加塤孔、拓展音域的實驗,在1984年之前他已成功研制出十孔陶塤。
曹正把自己燒制的塤贈送給同事和學生。由于他的積極推廣和他在古箏界的影響力與號召力,曹正做塤的消息逐漸傳開了。特別是1982年他的《塤和塤的制作工藝》(現代塤制作工藝的早期探索)一文發表以后,國內反響強烈,北京及外地的文藝工作者紛紛登門求教和索要塤。
曹正當時古箏方面的教學任務重、社會活動繁忙,但他熱情地接待了從四面八方趕來的造訪者。他當場演示,無償地傳授制塤技術,提供相關資料。他常說喜歡就是有緣,不管是傳授制塤技術或是古箏藝術,他沒有收過學生的費用。

他不僅在國內給演奏者傳授塤的制作和吹奏技術、將塤贈送給國內研究者作為研究中國古代音樂史和民族傳統音樂的實物,他燒制的塤還傳入美國、意大利、英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并參加了加拿大多倫多舉辦的中國古代藝術品展覽會。他的塤被日本大坂音樂大學附屬博物館收藏,博物志上寫著:“塤——中國樂器。制作者 曹正”。
這就是一代大師們的大氣風范和鉆研精神,致敬!
好了,今天的古箏名家趣聞故事系列就先到這兒吧,我們下回見咯!